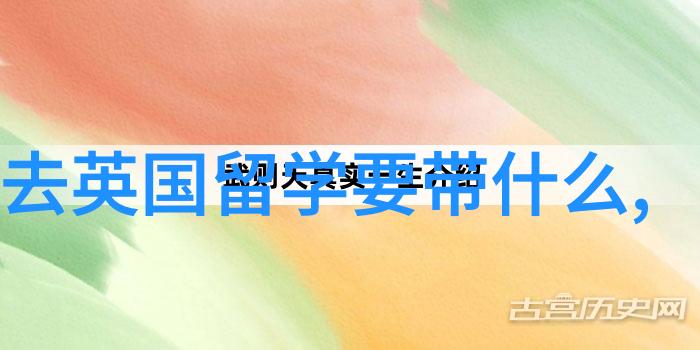我曾在十七岁的夏天,第一次出国门,去加州度过了几个周。那个时候,我有幸体验了西方盛行的远足——那些青山的缘故。在那里,我首次真正理解了“远足”这个词的含义。但当时我并没有喜欢这项运动,因为我更倾向于让他们扫兴,所以常常在那片片荒无人烟的丘陵地带走上四五个小时,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。我内心嘀咕着,那里怎么会有乐趣呢?但我的义父却一直对我说,“it's a lot of fun”。后来,当我自己旅行多了,我才明白所谓远足就是指长时间爬山。虽然我从未特别喜欢爬山,但中国的五岳和黄山竟然都是未涉足之地。

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,就算是一个智者吧,我就这么无赖地解释这个现象。虽然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古人对水与山会有智与仁的分法,但不知不觉间,我的远足次数确实越来越多,复杂的情感也是纯净的水域不可比拟。
又有一次夏天,我和龙姐去了香港,我们俩为了打发时间,在南丫岛进行了一次“远足”。别的人都去那里的港口吃海鲜,只有我们两个土人从岛的一头到另一头,这趟旅程花费差不多四个小时。那条路只有零星农民偶尔给我们指点方向,大多数时候觉得前方路遥遥无期,而且充满危机。我心里只想赶紧把这段愚蠢的事情走完,然后回到本岛去,也没有任何欣赏风景的心情。那个时候,“远足”变成了一个急着要完成的事务,对“何时了”充满绝望的一个代名词。

随后的旅行中,无论是婺源还是其他地方,每一次远足,都让我慢慢学会放下焦虑,一步一步往前走。一开始可能因为害怕而问很多人的路程,但是答案总是一样的:“很近。”直到真的看到了目的地,我们才会狂喜。这段旅程中的心理鼓励和减少恐惧,是帮助他人的唯一方式,没有漫长跋涉,也就没有晚上的美食和安稳睡眠。
后来,当脚力增强,不再需要赶上队伍的时候,我可以更加安然地掌握自己的呼吸,将注意力放在沿途风景上,有时甚至选择提早结束,不必登顶也可甘愿收兵。此刻,即便是在读商学院期间居住在大城市中,也很少机会进行远足;毕业后回到北京工作,与旧友重逢,他们邀请我一起与外国朋友去爬郊外野长城,那些年轻且勇敢的人,让我的视野被拓宽,让每一处新奇的地方都成为了探索自然之旅的一部分。

然而,在河北三界碑一次惊险的下坡过程中,我几乎失去了平衡,被Susan及时救回,这次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安全第一,更需要对自己的身体保持警觉,以及如何应对意料之外的事物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无论是讨教登山经验还是继续探索世界各地,或许还能遇见更多挑战,但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,那些青山,它们已经成为一生的知识、道德和灵魂力量来源之一。而尽管现在仍是我最爱海洋,但那些青山,却让我的生命变得更加丰富、简单,并赋予了勇气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。